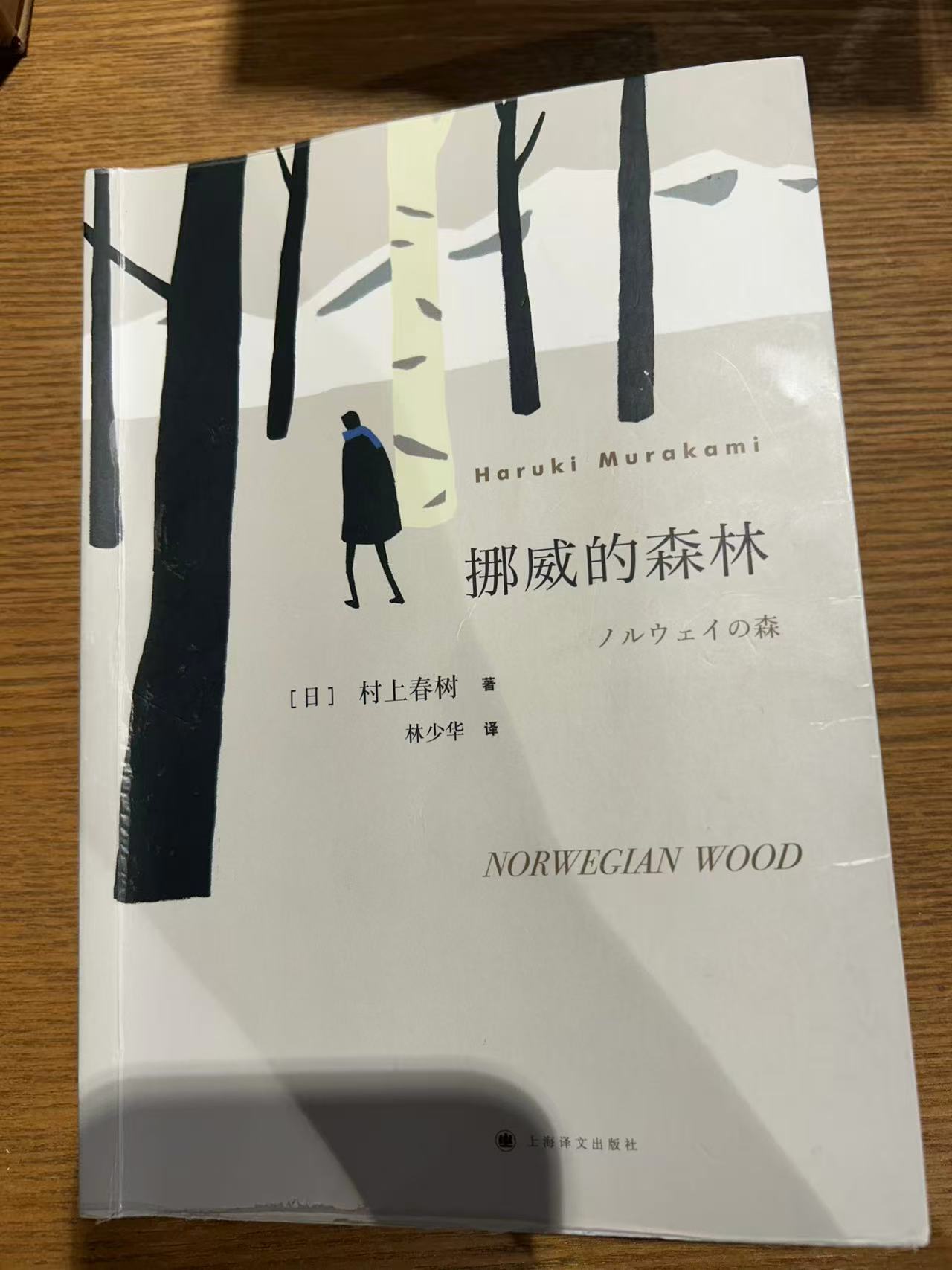《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
读完《挪威的森林》,不由自主想起日本那部经典电影《情书》。相比前者那种近乎放纵的克制,我反而更喜欢《情书》里那份克制后的错失,也许这是价值观的不同吧。
第一次接触村上春树大概是在 2013 年。那时我开始夜跑,而村上又是业余马拉松爱好者的代言人,于是读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时间久远,书中内容大多已模糊,而他挑战 100 公里超级马拉松的情节却历历在目。
从 2016 年才开始写读书心得,因此也错过了许多精彩与回忆。说起读书,那段青葱岁月总会浮现眼前。彼时,大学生真的是“天之骄子”,上了大学意味着真正的解放——60 分万岁,时间充裕,诱惑不多。再加上刚入学时情感上的一些困扰,我便用疯狂读书的方式麻醉自己。读的多是文学作品,当然也少不了金庸。大学前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小说,那时终于可以肆意阅读。
那时校园里还有许多小书店,店里最显眼的总是西方文学译著:《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飘》《战争与和平》《简·爱》……我几乎保持一周一本的节奏博览群书(唯独专业书除外——看数学书反而是在工作后才培养的习惯,颇为惭愧)。在那个改革初期的年代,“外国的月亮更圆”,西方名著一本本的读,再加上和某人一起看的那些经典西方电影录像(那时还是在图书馆借录像带看的),整个人仿佛都“西化”了。对《卡萨布兰卡》《罗马假日》《壮志凌云》之类的爱情片,当年的我并没有太深感触,不过女生大概都会喜欢吧。说到电影,又想起大学时代为数不多在菁菁堂看的《廊桥遗梦》。那时完全无法理解,一个老头和一位主妇的爱情故事,竟能获如此高评价。而如今却懂了——成年人的爱,来自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克制,比年轻时的炽热更显珍贵。
言归正传。
村上春树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挪威的森林》更是耳熟能详。但因为是言情小说,我这个重度理科男一直提不起兴趣。最近广州秋天气温忽冷忽热,阴晴不定,自己的情绪也随之起伏,莫名的多愁善感起来。前几天刷到书中的一些摘录视频,便突然生出了读一读的念头。
阅读过程中,我一直想到《第一次亲密接触》,想到痞子蔡,想到轻舞飞扬,想到那个早期 QQ 网恋的纯真年代。那时流行的是“你永远不知道对面是不是一条狗”;就像现在流行的“你不知道那个漂亮主播美颜背后是不是抠脚大叔,你也不知道安慰你的是不是 AI”。那个年代还会有轻舞飞扬,那时的网恋奔现也不会轻易“见光死”。回想那段青涩而克制的感情,虽然没有轻舞飞扬的悲情,虽然也充满遗憾,但如今再忆,那段时间连空气都是甜的。
《挪威的森林》扉页写着“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从一开始便笼罩着淡淡哀愁。幸好绿子的出现,让这片哀愁中偶尔闪现轻松与笑意。
渡边与直子的悲情,渡边与绿子的牵绊,还有玲子、木月、永泽、初美、敢死队……一群鲜活的青春面孔,却伴随着一首首悲凉的挽歌。
直子的疗养院像是“正常社会里聚集了一群所谓不正常的人”,而现实世界则像“不正常社会里住着所谓正常人”。在这混沌世界里,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似乎本就模糊。书中人物看似都不太“正常”,可或许每个人本质上都是不正常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那些放纵、多情的年轻人固然挣扎,但克制、理性就一定是正常吗?自古红颜多薄命,书里一个个祭日让人唏嘘。理性的“不正常”若能带来些许乐观,那就是,理性能成为保护壳,让人在这世界上艰难地自我维持。
过去的阅读偏好是计算机和数学专业书,其次是社科与管理,典型的 IT 男。但最近读了《一句顶一万句》《挪威的森林》,竟觉得自己敏感、悲观了不少。
以上便是《挪威的森林》的读后感,也算自己的青春回忆,写下来权作纪念。正如那句话所说:“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而如今,我终于有了后者。
最后,以某人最喜欢的苏东坡《观潮》作结: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文章精彩语句摘录
一部描写无尽失落和再生的
青春物语
《挪》即是死者的安魂曲,又是青春的墓志铭。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通过直子的死,明白任何这里都不可能治愈失去所爱之人造成的悲伤,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悲哀中挣脱出来。事实上渡边也最后穿越了那篇无边的泥沼和阴暗的森林,开始同现实世界接轨,摸索新的人生--借用村上的话,“所谓成长恰恰是这么回事”。
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概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越是模糊,我才越更能深入的理解她。
PS:记忆越是模糊,越能看到本质。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送走了十八岁的春天,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隐约感觉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词。但无论我怎样认为,死都是深刻的事实。在这令人窒息般的背反性当中,我重复着这种永无休止的圆周式思考。如今想来,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居然凡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的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唯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摸一下发卡,或用手绢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一把紧紧地搂在怀里,却又总是怅惘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伤害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寻找语言。
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途中。
(渡边和绿子的搞笑对话)
“图书室。“我说。
“别去那种地方,和我一同吃午饭去如何?”
“刚吃过。”
“那有什么,再吃一次就是”"嗳,那边那个拄松木拐杖的老头儿,我们一进来就鬼鬼祟祟地往我腿上看,就那个穿蓝衣戴眼镜的老头儿。"绿子不无陶醉地说。
“当然要看,穿那样的裙子谁都得看。”
“不过也蛮好嘛,反正大伙都无聊之极,偶尔欣赏一下年轻姑娘的腿调剂调剂也好。兴奋起来促进康复也未可知。”
“但愿别适得其反。”我说。喝完咖啡,我和绿子折回病房。她父亲还在酣睡,凑上耳朵听听,尚在微微喘息。随着午后时间的推移,窗外阳光的色调变得柔和而沉静,一派秋日气息。小鸟成群结伙的飞来,落在电线上,又一忽儿飞去。我和绿子两人并坐在屋角处,压低声音说个不止。她看了我的手相,预言我能活到一百零五岁,结婚三次,最后死于交通事故。我说这一生还算不赖。
"月经一来,我就戴两三天的红帽子。这回能知道了吧?"绿子笑道,“我一戴上红帽子,你在路上遇见也别打招呼,赶紧逃命。”
“那不是努力,只是劳动。”永泽断然说到,“我所说的努力与这截然不同。所谓努力,指的是主动而有目的的活动。”
“举例说,就是在职业确定之后其他人无不只顾庆幸的时间里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是这样的吧?“
”正是这样......“"我同渡边的相近之处,就在于不希望别人理解自己。"永泽说,“这点与其他人不同,那些家伙无不蝇营狗苟地设法让周围的人理解自己。但我不那样,渡边也不那样,而觉得不被别人理解也无关紧要。自己是自己,别人归别人。”
PS:
"蝇营":说的是像苍蝇那样四处飞动,营营往来,追逐污秽之物。这个意象其实更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小雅》中的《青蝇》篇,用"营营青蝇"来讽刺进谗言的小人。
"狗苟":则是形容像狗那样苟且偷安,不顾廉耻地活着。
韩愈将这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蝇营狗苟"这个成语,生动地刻画了那些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四处钻营、卑鄙无耻的人的嘴脸。围绕着“为什么手的中指比食指长,而脚趾则相反”的问题讲授一番。
倘若周围一团漆黑,那就只能静等眼睛习惯黑暗。
更何况我仍在爱着直子,尽管爱的方式在某一过程中被扭曲得难以思议,但我对直子的爱却是毋庸置疑的,我在自己的心田中为直子保留了相当大一片、未曾被别人染指的园地。
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熟知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法排遣这种悲哀。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